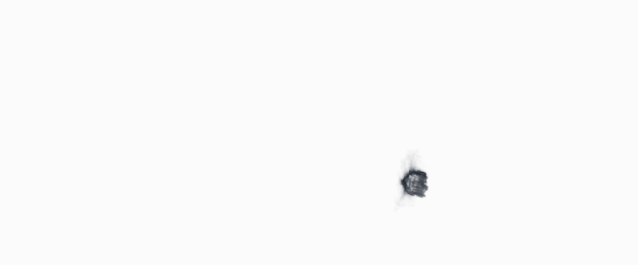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20日至2月27日,Y某使用其妻子的证券账户陆续买入X股票70余万股,交易金额470余万元,X股票于2020年3月2日公布定向增发方案,定增公告后,X股票大涨,Y某陆续卖出X股票,盈利360余万元。
证监会认定,涉案X股票的定向增发属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为不晚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于2020年3月2日。2020年6月,Y某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之后变更为监视居住。
2022年2月,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指控:在X股票所涉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知情人V某于2020年1月17日来到Y某所在城市并与Y某等人(同为D公司股东)在某饭店参加D公司团拜会,1月18日中午,V某与Y某共进午餐。公安机关认为,Y某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情节严重,涉嫌内幕交易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如果Y某被认定内幕交易罪,将会面临最高十年有期徒刑的处罚,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并向Y某复核证据及事实,认为本案证据以言词证据为主且矛盾证据较多,案件事实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法律适用亦存在较大争议。经团队数次研讨,认为Y某与V某接触之时,V某还未获知内幕信息,Y某即便获取了内幕信息,其来源也并非V某,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错误,另外,Y某所获取的信息更可能为二手信息且被认定为内幕信息的证据可能不足,遂向检察机关提出证明Y某涉嫌犯罪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一、事实认定之辩:Y某的信息并非来源于内幕信息知情人V某
公安机关指控Y某涉嫌内幕交易罪的理由是Y某从知情人V某处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并根据信息进行了交易,而根据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2)(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的规定,认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方式有三种,即:非法手段型、关系密切型和积极联络型。
就本案而言,并无证据证明Y某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故Y某不能被认定为非法手段型,那么,Y某是否属于关系密切型或积极联络型呢?经辩护人分析,Y某与知情人V某在敏感期内确实存在接触的情况,如果Y某的内幕信息来源于V某,则较大可能被认定为关系密切型或积极联络型。但经梳理分析在案证据,发现V某最初知晓内幕信息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20年2月16日,也即在二人接触之后,具体理由为: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但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在2020年2月16日之前,V某并不知晓案涉内幕信息。如,V某称:2020年2月16日,Q某让我准备一笔钱,她告诉我公司要做X股票的定增,我当时还不信,专门问了W某,他说是做X股票的定增,这时我才知道公司参与X股票的定增项目。W某称:X股票定增过程中我没有给V某说过,直到2020年2月16日,V某问我定增的是不是L某的公司,我才告诉他X股票定增的消息,我要求他保密。同时,V某与W某、Q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印证V某、W某和Q某的上述说法。前述证据充分证明V某知晓定增对象为X股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16日。
因此,虽然在案证据显示2020年1月17日-18日,V某与Y某有过接触,但此时V某对案涉内幕信息仍不知情,尚不属于知情人,与Y某的接触并不会导致内幕信息的泄露。而2020年2月16日(V某被认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之日)之后,在案证据又不能证明二人有过接触、联络,因此,在案证据不能证明Y某的信息来源于V某,Y某不应认定为关系密切型或积极联络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
Y某的信息来源于同案嫌疑人C某的推荐股票。
Y某与C某系朋友关系,C某与V某也是朋友关系。关于为何要购买X股票,Y某称:“我的一个朋友C某在今年年初(我购买X股票前不到一周)说X股票还不错,而且H基金(案涉定增基金)在2019年下半年也考察过这家公司(具体是怎么考察的他没说),但是最终两家公司没有合作,他说虽然没有合作成,但是这家公司还可以。”而C某并非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所传递的信息也存在模糊性,甚至否定H基金定增X股票,因此只能认定是一种推荐股票行为,不能认定为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同时,根据在案证据,辩护人提出Y某购买X股票较大可能系基于朋友C某的推荐以及网络信息(Y某提供了其在购买X股票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了“X股票可能会大涨”的分析意见)的综合分析,并非基于内幕信息进行的交易,因此本案Y某既不符合犯罪主体要件,也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二、法律适用之辩:二手以上内幕信息获取人并非本罪处罚对象
为保证本案的辩护质量,经团队研究后决定,在提出本案事实认定存在的问题后,应从法律适用角度进行研究,寻找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出路。之后,辩护人对本案事实进行模型建构,假设C某被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即“一手”内幕信息获取人),C某向Y某推荐X股票的行为被认定为泄露内幕信息,那么Y某是否应被追究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呢?即,“二手”及以上信息获取人员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罪?经分析,辩护人认为,“二手”及以上信息获取人员不属于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认定二手及以上内幕信息获取人构成内幕交易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及《内幕交易解释》规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从文义解释角度而言,除“非法手段型”,只有直接从知情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才能被认定为“关系密切型”“积极联系型”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即“一手”内幕信息获取人),从其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者(即“二手”内幕信息获取人)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也即,关系密切型或积极联络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必须是从知情人员处获取的“一手”信息,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再次泄密,“二手”或“三手”被动获知信息的人员不构成该两种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主体,此种行为人若按照内幕交易罪定罪处罚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理念也不相符合。[1]因此,即便推定Y某获知了内幕信息,其信息来源最大可能为C某,而其系被动获知,也并未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且C某并非本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因此不能认定Y某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更不能将Y某认定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
第二,将Y某认定为内幕交易罪与司法实践掌握标准相悖。辩护人通过查阅裁判文书网及其他网站,对全国范围内内幕交易犯罪判决情况进行检索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辩护人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非法获取”为检索条件,检索到有效案例共计34件,综合分析裁判案例得出“司法实践中对'二手'获取内幕信息并独立进行交易的行为基本是不予定罪处罚”的结论,具体分析如下:
1.25件案例仅处罚直接从知情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并交易的非法获取人员。该25件案件虽仅处罚了知情人及一手非法获取人,但案情也涉及第二手或以上的传递及交易者,但该类人员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认为,司法裁判人员之所以作如此考虑,原因之一便是将二手及以上信息获取人员列为犯罪打击可能导致打击范围过大。
2.4件案例未将二手信息获取并进行独立交易的人员认定为犯罪。经查阅案例,陈建龙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5)浙刑二终字第96号],茹振刚、张彩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二审刑事判决书[(2019)粤刑终1221号],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20)皖刑终16号],满某某、孙某甲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鲁05刑初14号]裁判文书显示,前述案件的一、二审判决书均未将二手传递者作“另案处理”表述;同时,相关案件中的二手传递者是作为证人列出;可见,前述案例对内幕交易的二手传递者的处罚是持否定态度的。
3.2件案例虽处罚了二手信息获取人员,但均是依据共犯原理进行处罚。前述案件中,二手信息获取人并未独立依靠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是帮助一手非法获取人员进行交易而获刑。其中,王泽志、张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沪02刑初22号],对二手获取信息者的处罚依据是其从一手非法获取人员处得知信息后,帮助该一手非法获取人员买卖相关股票;王忠仪、王毅红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闽05刑初92号],则是一手非法获取人员将信息告知其妻,并指示其妻实施买卖股票的相关操作。故该两案例,仅是通过共犯理论来处罚二手信息获取人员,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认可二手信息获取人员获取内幕信息后独立交易的行为能够认定为犯罪。
另外,所有公开案例中,仅倪鹤琴、胡宁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二审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51号]一例,是将二手获取内幕信息并交易的人员,按照“非法获取人员”认定进而认定其犯内幕交易罪。但辩护人认为,其一,该案仅是个例,并不具有参考性或代表性;其二,该案不仅与其他众多案例呈现的司法认定规则不符,也与广东高院的后续判决观点(2019年茹振刚、张彩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二审刑事判决书)相悖,广东高院仍坚持了不应将“二手”及以上信息获得者定罪处刑的观点。
综合前述分析,辩护人认为“关系密切型、积极联系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不应包括“二手”及以上内幕信息获得者,对该类人员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进而不能对该类人员定罪处刑。
案件处理结果
某检察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观点,本案经退回公安机关二次补充侦查后,认为证明Y某涉嫌内幕交易罪证据不足,并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无法证明Y某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且无法排除相关交易具有其他正当理由或者正常信息来源可能”的观点,依法决定对Y某作证据不足不起诉处理。
结语
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国家不断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提出以刑事手段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近期,两高与公安部、证监会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彰显政府监管资本市场,打击犯罪的决心。鉴于资本市场违法犯罪具有专业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往往涉及人员众多,可能导致追责范围不当扩大,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希望本文可抛砖引玉,为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些许参考。
注 释
[1] 参见:“在传递型内幕交易犯罪中,对于二手以上人员不宜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既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也不会出现打击面扩大的问题”——《内幕交易案件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报,2016年09月14日
律师简介




